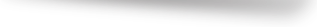国庆
4
号到
6
号关于“生存即关怀”的工作坊算是我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参与到接触即兴,几天过去,每当听到《
Mondo Bongo
》的音乐响起,身体仍然情不自禁涌起跳舞的冲动。一直以来,我想要思考如何将具身性带入文本的写作之中。舞蹈和对舞蹈本身的写作如何交织在一起,身体、触感、剧场性如何能够与书写共在,或者说,这种多重维度的同时性该如何发生。
法国哲学家让
-
吕克·南希(
Jean-Luc Nancy
)在《身体》(
Corpus
)中这样解答关于身体、触感与书写的关系:「触及身体,触摸身体,触感——始终发生于书写。」
「沿着身体的边界,在它的极限,它的末端,它最远的边缘,只有书写发生。」(
Corpus, 2006, p.13
)
在身体的边界处、在身体的最极限处,所发生的只有书写。对于身体来说,身体的意义恰恰来自书写。书写不是为了记录和再现,而是为了触感;书写本质上是对身体的触及、生成和打开,是一种不断触及身体界限的触摸方式。而身体的意义正来自于对身体的触及与触感,身体通过触感获得实体性的主体感知。
然而书写在不断触及身体的同时,身体本身却永远无法被真正书写和阅读,对身体的书写实质上是一种不可被阅读的文字性——身体只是处于皮肤的表面:「身体,从一开始就是块体,是被呈奉的块体,没有什么可以表达它们,没有什么可以连接它们……它们没有中心,没有黑洞,它们就在皮肤的表面。」(
Corpus
, 2006, pp.74-75
)

摄影:
Ella Yang
身体拒绝着被书写和思想表征,它只属于皮肤,属于表皮,属于触摸的激情。和南希一样,德里达曾在「触」(触摸、触感、触动等等)中发掘处出一种「激情」的意义,它既是对激情的触及,也是触及本身的激情。
真正属于身体的书写也是一种对表皮的激情,一种对皮肤的触摸的激情。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即兴舞蹈本身和对即兴的写作一样,都可以实现一种属于激情的身体书写,这种激情属于皮肤和表面。
人的身体终究有多少种可能性?那种在词语和语言之外、只属于身体本身的可能性。
Zoe
老师说一个学员曾和她说,想去尝试在每一天早上以一百种不同的方式起床,这是一句被当时的我很快忘却、事后想来却又异常感动的一句话。不仅仅是起床的方式有千万种可能性,还有走路,如何从这里的一点走向那里的一点,如何从床上走下,如何拿起一个水杯。身体竟是夺回想象力最大的潜能之地,有千万种可能性栖居于此。
对于初次接触到
CI
的我来说,我兴奋于一种未知的、或许是即将到来的可能性:
我们该如何通过
CI
重新学习日常生活、并与这个世界重新建立一种崭新的关系?
我想要用一切具身性的身体艺术重新学习日常生活,包括舞蹈、戏剧和表演艺术。在接触即兴中,我们学习着将自己完全卸下交给重力,伴随着重力和接触点的变化转换着身体的姿势;我们学习着将自己的身体完全交给舞伴,而不保留着对自我的控制和用力。我们可以和这个世界保持怎样一种关系呢?是用力的关系、紧张的关系,还是一种触觉的亲密的关系、一种可以完全信任的关系、一种消解着二元对立的关系。

从左至右:Yi、Harden 、觉非、怡宁、勇者
摄影:
Ella Yang
接触即兴是如此具有潜在性,它让日常中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发生。身体可以生成为什么?一个水袋,一只蜥蜴,或是一个风筝,一个魔方……第一天,
Zoe
老师带领我们从楼梯上模仿水流一点点滚下,楼梯在日常中是坚硬的,但是当身体不再是日常中作为客体的身体,而是生成为水流时,流动的可能性便会发生。同样,当一个舞者熟练地使用她的接触点背起一个重量更大的舞伴时,身体也不再是在日常中被各种不可能和规范性界定的身体,而是随时可以召唤出新的潜能。
如果视觉的凝视总是带着评判性和审视性,那不如闭上眼睛,信任自己所触摸到的一切,在对当下的专注中回到生命最原初的状态,像一个孩子一样觉察着自己和他人的每一个动作,以及在这个空间中如其所是发生着的一切。还记得在第一天工作坊结束之后,我们在
Heim
酒馆跳着盲酱,我在瞬间感受到了白天不曾感受到过的专注,仿佛在那一刻,身体可以真正将时空填满。

摄影:Ella Yang
工作坊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即兴中写下了一首诗。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身体总是在呼唤着文字的介入:
他们坐成了一个圈,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进入所有的人。
Dancing partner,
你有怀疑过语言和生存本身吗?
Dancing partner,
我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再一次感受到了空虚和无意义。
Dancing partner,
你为什么总是对他人的在场感到不安?
我被淋湿了,从空间里涌动而出的海水弥漫在每一个舞者身上。
Dancing partner,
你为什么而跳舞呢?
有什么东西醒了过来,我听到他们衣服滑过皮肤的摩擦声。
Dancing partner,
我想要寻找形式,可终究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承载内心的渴求呢?
他们快速地在空间里走来走去,之后他们突然停止,以最慢的速度倒下。
Dancing partner,
我为什么总是没有办法完全地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很多种颜色相遇在一起,绿色的上衣,紫色的裤子,棕色的头发,白色的袜子。
Dancing partner,
人与人之间真的可以实现最为赤诚的交流吗?
她做出水滴的动作,而他跟随着水滴流转,像是在她身旁的一块吸铁石。
Dancing partner,
什么才是最为根本的呢?快乐,还是痛苦。
她们在地上缓慢地翻转,直到音乐已经前进了三个重复的段落。
褶玉与Kiki 摄影:胡一帆
一个人在追问着看上去最为抽象、最被困扰的、很沉重的哲学问题;另一个人则看上去只是在漫不经心地描述着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描述着我们在做的事情本身。到底什么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流?好像总是很难以向他人问出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而只能很生活化地在交流一些属于表象的经验事情。可是这种停靠在皮肤的接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不可能性吗,还是另一种深邃之处。
在我们思想之前,在我们开始追问开始困惑之前,我们已经通过身体存在于世,我们已经在现象界中开始了彼此的接触。或许我们不必一定要去解答什么,去完成去实现什么,我们只需去感受,生活,去尽情地跳舞。